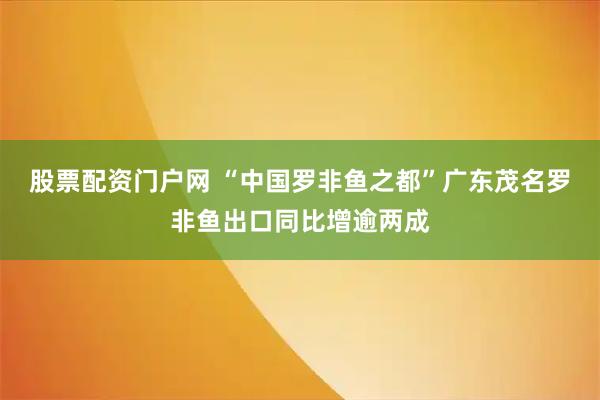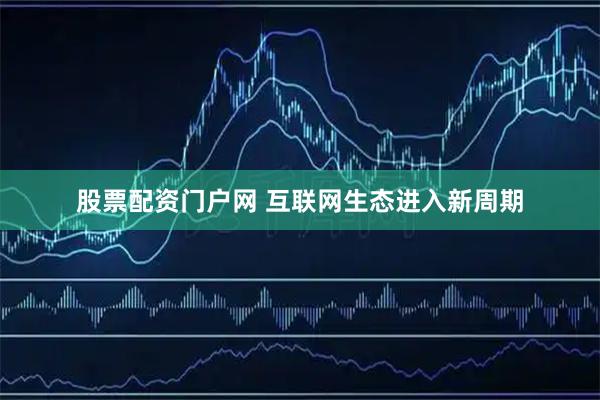人民路上的怡园里,一棵百年石榴树新晋“网红顶流”,霸屏了社交媒体。
怡园,在苏州园林中,论资排辈,居“晚生后辈”,只廊壁嵌有王羲之、怀素、米芾等多名书法大家的101块石碑作为“镇园法帖”。古宅、古园里的楹联碑志,一如历史的散简断编,逐一读去太过劳神费心,我向来无心细看,宁可站在一棵百年古树下,静静仰观,那遒劲有力的树干,将虬蟠纵横的枝柯和鳞集森然的细叶托举到苍穹中去干预风云,其姿宛若游龙从平地上腾空而起,盘旋缠绕,直冲霄汉。
初秋的榴果,胭红灼灼,像一盏盏“秋日限定灯笼”,缀满枝头,掩映在黛瓦、白墙、朱阁、绮户……就像古画中一抹朱砂般点睛之笔,长在了国人的审美点上,令人惊艳到屏息,无怪乎,不少游客跨省赶来,只为一睹其芳姿。摩掌树身,每一道纹路都是光阴的刻痕,每一次摇曳都是无言的低吟。
我相信,古树是有生命的,更是有灵魂的。作为一名情绪低落、形如槁木的职场失意人,我驻足良久,似乎从它身上读懂了什么叫生生不息。百年轮回,迎来客往,它阅尽人世间生荣死灭、甘苦悲喜,甚至看得厌倦了。可人世间的那点事,无论遭逢天灾重祸,抑或暂时被阻抑,但凡留存一线生机,终会有抬头的日子。
忽而,头顶黑云弥漫,天际闪出一道电光,紧接着发出隐隐的闷雷声响,骤然之间,“劈里啪啦”洒落下一场瓢泼大雨。骤雨初歇,石榴皮上浮漾着湿湿的浅光,把王维诗句中“夕雨红榴拆”具象化了,看得我舌底生津,遂想学起“宵来酒渴真无奈”的徐文长“唤取金刀劈玉浆”。
记得小时候,叔祖母搀着我逛菜场,门口摆摊的老妪白发稀疏、满脸褶皱,与叔祖母年龄仿佛,她一身蓝布,头上包着一方蓝印花布。她坐在两担沉甸甸、红彤彤的石榴中间,这个岁数的城里老太太,早该在家颐养天年、含饴弄孙了。叔祖母和老妪闲聊几句,老太太是洞庭西山村民,石榴熟了,她每天早早起床,乘坐从西山到市区的公交车,蹲点菜市场门口,卖完石榴才收摊,来回颠簸四五个小时。其实,苏南富庶,乡下人承包田地、果园,小日子红红火火。老人说,她劳碌一辈子,手脚“闲不住”。叔祖母瞧着她佝偻的背,怜老惜“贫”之心顿起:给我小孙女挑两个吧!
老太太仔细挑了两个又红又大的石榴,塞我手里:这是自家种的石榴,包甜!不甜不要钱!
回到家,叔祖母取出水果刀,切开顶盖,沿着果皮筋络切成几瓣,而后撕开薄膜,小锤子轻轻一敲,一场绯红的“石榴雨”落在洁白的瓷盘里,籽儿晶莹剔透,色如玛瑙,舀一勺放口里,上、下门齿轻轻一叩,浆汁急不可待地爆裂而出,一股子清甜爽口从舌尖直抵喉间,又不会甜到发腻,所谓“嚼破水晶千万粒”,每一口都像是吮吸着鲜榨果汁,初秋的燥热在这一粒一粒的榴籽缠绵厮磨中消失殆尽……
江南人的中秋,桌案上摆置着“四大金刚”:清蒸大闸蟹、桂花糖水鸡头米、月饼、石榴。先用“蟹八件”剔、夹、叉、敲……逐次取出橘红的蟹黄、乳白的蟹膏、雪花状的蟹肉,蘸上调好的“葱姜醋”,放入嘴里,丝丝缕缕蟹鲜味在唇齿间荡漾开来。吃完螃蟹,再来一碗桂花糖水鸡头米,软糯弹牙、嚼劲十足,汤水里带着沁人心脾的桂花味,芳香溢齿,甘泽润喉。末了,剥一只石榴,或与家人碎碎细语,或追一部治愈系影视剧,或肆意发呆、消磨秋光。
茶舍传来弦琶琮铮的苏州评弹《三笑》,想起评书中一位诙谐人物——石榴姐姐(华府丫鬟),她相中了府里新来的一个眉清目秀、才华横溢的小厮华安(唐伯虎乔扮的),春心荡漾,对着唐伯虎发花痴、单相思,自吹她与华安同年、同月、同日、同乡的“四同”关系,便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此时,一顽皮孩童股票配资门户网,抬起脚,冲着屹然峭起的老石榴树猛踢数下,树身岿然不动,倒是疼得孩子龇牙咧嘴。人,虽被奉为“万物之灵”,可在阅历资深的老树看来,不过是绕树追逐的燕雀、转瞬即逝的过客耳,难以望其项背。数十年、数百年之后,皆尘归尘、土归土,唯那一树石榴红,与名园同寿、与天地俱老。
配先查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